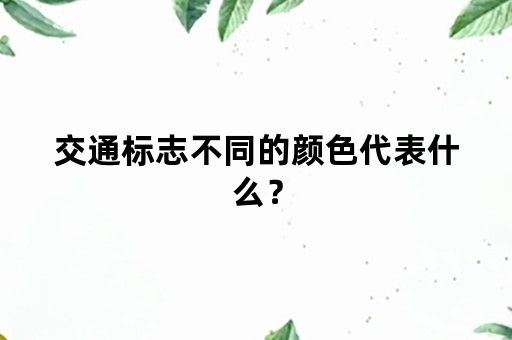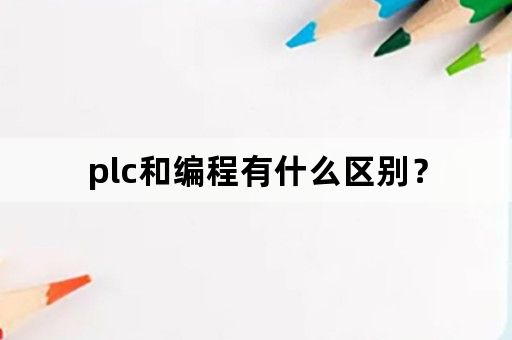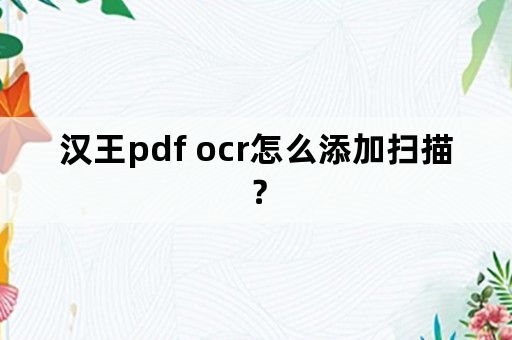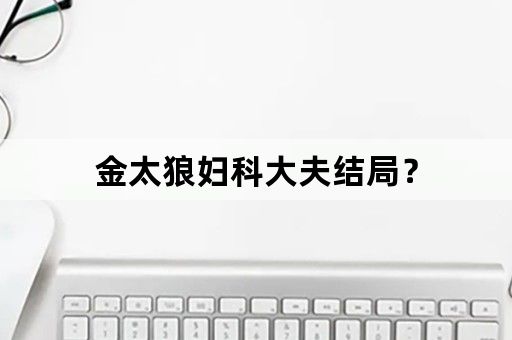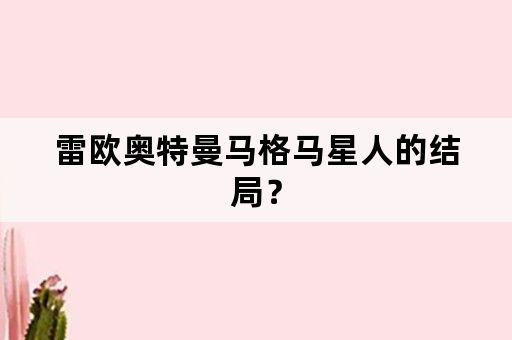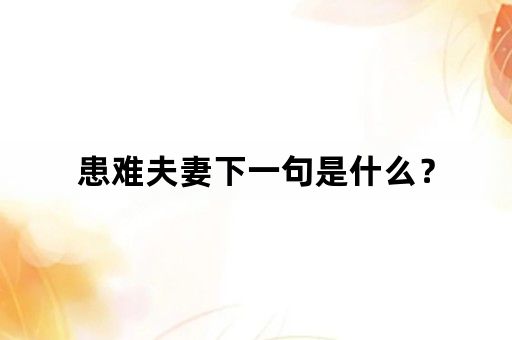首先,问题的表述有误,清朝是旗人统治,并不是满族人统治。旗人中包括蒙八旗和汉八旗,此外还有内务府三旗,还曾将俘虏来的俄罗斯人编为一旗。
民族国家意识是后来才诞生的,此前虽有民族意识,但不像现代人这样带有强烈的“他者”的眼光。
比如雍正时,曾有三次“出旗”,给多余的旗丁田地,让他们成为普通农民,从此不再是旗人,出旗是为了精兵简政,其中汉军旗的人较多,但也有满军旗。
清政府对满人确有较多照顾,但到乾隆时,对穷满人已基本放任自流。
满人自视高人一等,歧视其他民族,在制度安排上。确实存在不同民族不同待遇的情况,但汉人与旗人有暗中流动的管道,且二者的分别越来越模糊。
比如晚晴重臣托忒克·端方,他被杀前曾承认自己是汉人,原姓陶。再比如曹雪芹,他是旗人,所以他死在免费住的旗房中,还曾在宗学中教书,《红楼梦》初期是在旗人中流传,汉人了解不多,当时文坛领袖龚自珍对《红楼梦》有评价,但一听就知他并没看过。目前能找到的《红楼梦》早期版本,都在旗人圈中流行,可曹是典型的汉人。
刘小萌先生曾对乾隆后北京八旗社会进行研究,并有专著,认为满汉通婚日渐增多、文化互相交融,远不是今天我们语境中所理解的“民族压迫”。
强调满清异族,源于“新清史”,将清朝视为拥有近代意识的国家,比如“国语骑射”,比如“下马必亡碑”,比如堪舆全图,都证明清朝统治者有近代民族国家意识,所以应从民族压迫的角度来理解清代。“新清史”确有新见,让人耳目一新,但常有生搬硬套之弊。
其次,康梁等恐怕也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立宪制。
清末时,满族、汉族、蒙族等已相处200多年,尤其是经康乾盛世,社会基本安定,事实证明,民族本身并不是问题,只有当外部环境恶劣时,民族才成了一个问题。
到康梁时,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持天下意识,并无多少民族国家意识,如果一定要用现代的尺度来衡量他们,林则徐、曾国藩不也一样在为清廷服务吗?只能说,大家已和睦生存了许多年,彼此已成一体,有了共同的价值认同、文化认同,非要从现代人的民族国家观出发,投身于反满大业,这恐怕与历史的具体情境相悖。
如果非要纠缠于此,那么历史上有个纯粹的法兰西族吗?有纯粹的英格兰族吗?毋宁说,民族本身就是建构而成的,它与血缘无关,与共同的历史与文化认同相关,非要纠缠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”,那世界上“纯而又纯”的民族国家能有几个呢?
立宪与民族主义有一定关系,后者为前者提供合法性,但看康梁的奏折就可知,他们基本搞的还是法家那一套,对现代政治了解不多。
满清统治华夏267年,早已在文化上融于汉文化,但却空前加强君主专制,汉人先后经过剃发令,文字狱的荼毒,基本上臣服于满清的皇权,再加上政治上的满汉牵制限制,读书人,宦官仕子早也没有了满汉正统(华夷之辩)之分,很多在政治高压下已经被有意识的塑造成为皇权服务的奴才,在他们心中荣华富贵和生存才是第一位的,至于民族的危亡,国家的前途那是皇帝的家事,他们也不敢也不想管,正是由于满清皇帝成功的制止了华夷之辨,重新解释了胡汉正统的命题,才稳固地统治中国200多年,这与其超前的战略思维分不开,但也仅仅是作为入住中原的名分解释,要不然也不会经济发展,政治不断到退了